集資(zī)詐騙案件在近些年呈現一(yī)定的井噴之勢,該類案件的頻(pín)發嚴重擾亂了國家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巨大(dà)的社會危害;同時圍繞着集資(zī)詐騙罪司法判決産生(shēng)的争議也日益增多,很多案件并沒有因爲終審判決的做出而塵埃落定,對集資(zī)詐騙在罪與非罪上的正确厘定和準确性質定位便變成了當下(xià)司法實踐不得不解決重要議題之一(yī)。
一(yī)、集資(zī)詐騙罪概念的厘定
對于集資(zī)詐騙罪概念内涵和外(wài)延的理解往往成爲司法實踐中(zhōng)對該類行爲性質定位的關鍵,它在很大(dà)程度上決定着該罪司法認定中(zhōng)關鍵性問題的尋找,進而從根本上決定着該類行爲罪與非罪的認定。我(wǒ)國刑法界的通說認爲,集資(zī)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爲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zī),數額較大(dà)的行爲。{1}與之相應的觀點認爲,集資(zī)詐騙是以非法占有爲目的,非法集資(zī),騙取集資(zī)款,數額較大(dà)的行爲;{2}或是以非法占有爲目的,使用非法集資(zī)方法進行詐騙,數額較大(dà)的行爲。{3}從刑法學界的通說以及刑法第一(yī)百九十二條和第一(yī)百九十九條(南(nán)京刑事注:本條根據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刑法修正案九删去(qù))的相關規定來看,集資(zī)詐騙罪在客觀上是由詐騙他人錢财和非法集資(zī)的行爲複合而成。将以非法占有爲目的,用虛構事實隐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私财物(wù)并幹擾正常金融秩序的行爲。進而可以看到集資(zī)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主要爲以下(xià)三個方面:是否以非法占有爲目的、是否采用詐騙方法以及是否非法集資(zī)(主要指是否向不特定多數人非法集資(zī))。
二、集資(zī)詐騙罪司法認定的“黃金三條”
筆者認爲,集資(zī)詐騙罪的關鍵性構成要件即是否以非法占有爲目的、是否采用詐騙方法以及是否非法集資(zī),恰恰是以上三點構成了司法實踐中(zhōng)對該類行爲罪與非罪的性質認定的關鍵,對上述三個概念的正确厘定成爲此類案件司法認定的“黃金三條”。
(一(yī))對“非法占有”的正确厘定
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tǐ)适用法律的若幹問題的解釋》就有所提及,在這個解釋中(zhōng)的(2)(3)(4)項的相關規定以無法返還的結果作爲推定非法占有的原因,在司法實踐中(zhōng)對于非法占有的厘定起到了很大(dà)的作用,然而其本身也存在很大(dà)漏洞。我(wǒ)們知(zhī)道“并非所有‘無法返還’的結果都能推出非法占有的原因,例如,行爲人因不可抗拒力(天災人禍等)等原因,導緻無法返回集資(zī)款,就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時還會出現另一(yī)個問題,如果行爲人揮霍了集資(zī)款或者使用集資(zī)款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但在案發後能夠還上,是否就可以認定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很明顯這種推理不能使人信服,并且使人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則産生(shēng)質疑,畢竟定罪量刑依據的是主客觀相一(yī)緻的犯罪事實而不是犯罪後誰更有錢。”{4}在2001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gōng)作座談會紀要》和随後修訂的司法解釋已經很大(dà)程度上解決了這一(yī)問題,特别是在處理拒不返還這一(yī)結果推定上,堅持了主客觀相統一(yī)進行非法占有的性質定位,不能僅從無法返還的結果進行認定,還要重點從無法返還的原因進行分(fēn)析,防止純粹的主觀判定。
筆者認爲,非法占有的主觀方面是通過客觀行爲表現出來的,因此認定非法占有也必須依據行爲來認定,但隻有在依據客觀行爲推定出的主觀心理狀态是唯一(yī)的情況下(xià),這種推定才是可取、可行的。所以對于上述認定依據不能僅從無法返還的結果來認定,還需從導緻無法返還的直接原因來分(fēn)析,如果主觀上并沒有惡意經營而出現無法返還的現象,即客觀原因導緻的不能作爲進行非法占有認定的原因。
從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來看,以下(xià)7種情況視爲“非法占有爲目的”:(1)明知(zhī)沒有歸還能力而大(dà)量騙取資(zī)金的;(2)非法獲取資(zī)金後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zī)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zī)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zī)金、隐匿财産,以逃避返還資(zī)金的;(6)隐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産、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zī)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zī)金、拒不返還的行爲。
參照上述司法解釋,在如何認定“非法占有”這一(yī)概念時,(2)、(4)、(5)對于非法占有的性質認定更加側重于客觀認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上述三種情況下(xià)行爲的性質定位是顯而易見的。我(wǒ)們再從上述司法解釋的(1)和(3)來展開(kāi)對該問題的探讨。(1)中(zhōng)前半部分(fēn)提到“明知(zhī)沒有歸還能力”是一(yī)個主觀性很強的認定,切忌從最後無法歸還的結果上進行推定,應當注重從最後無法歸還的原因進行定位,如果是由于人爲原因故意或惡意導緻的,就需要結合案件的具體(tǐ)情況進行是否屬于非法占有的定位,反之,不能草率的做出一(yī)個魯莽的特别是随性而爲的推定。在進行相關認定時,要注意區分(fēn)惡意和正常的商(shāng)業風險,不能将常态的商(shāng)業風險當作惡意經營,隻要經營的風險沒有高于一(yī)般商(shāng)業投資(zī)的最高風險,便不能将這種風險導緻的無法歸還認定爲非法占有;對于(1)中(zhōng)後半部分(fēn)的“大(dà)量騙取資(zī)金”需要進行正确的厘定,因爲“騙取”屬于一(yī)個主觀性很強的概念,切忌在司法案件中(zhōng)将借款的策略當作騙取,應當嚴格區分(fēn)非法集資(zī)中(zhōng)非法占有爲目的的誘餌和正常借款中(zhōng)的高許諾帶來的誘惑。同時,從非法集資(zī)的特征來說,非法集資(zī)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容易蔓延,犯罪分(fēn)子騙取群衆資(zī)金後,往往大(dà)肆揮霍、隐蔽,而對于正常生(shēng)活中(zhōng)借款策略風險承諾的隐蔽性是顯而易見的,切忌将借款過程中(zhōng)那種或多或少的帶有欺騙性的言行,認定爲詐騙;從(3)來看,“肆意的揮霍”應該是不計成本、不講目的、不講回報的大(dà)規模花費(fèi),從司法實踐來看,需要将上述肆意揮霍的行爲和商(shāng)業上的經營策略做出嚴格的區分(fēn)。在商(shāng)業的經營上,很多公司或個人爲了吸引公衆的眼球或博得大(dà)衆對其商(shāng)業上的認同,往往采取“一(yī)擲千金隻爲搏美人一(yī)笑”的經營策略。這種情況下(xià)需要将公司一(yī)擲千金和其實際承受能力結合來考慮。如果這種經營策略已經超出公司的能力範圍,這種行爲是否屬于肆意揮霍就需要結合案件的詳情做進一(yī)步的認定,相反,隻要這種一(yī)擲千金的行爲沒有超出其能力範圍,并且采用這種言行屬于經營策略,便不能将這種行爲認定爲肆意揮霍。
(二)“詐騙“的準确性質定位
陳興良教授認爲:“所謂‘使用詐騙方法’是指行爲人以非法占有爲目的,編造謊言,捏造或者隐瞞事實真相等欺騙方法,騙取他人資(zī)金的行爲。”{5}關于本罪的詐騙方法,《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tǐ)應用法律的若幹問題的解釋》也進行了界定,即詐騙方法是指行爲人采取虛構集資(zī)用途,以虛假的證明文件和高回報率爲誘餌,騙取集資(zī)款的手段。
由上可知(zhī),對于詐騙的定義不僅存在着不全面的問題,而且存在着指代不明的情況。現實生(shēng)活中(zhōng)詐騙的方法錯綜複雜(zá)、花樣百出,司法解釋也很難将其全部囊括其中(zhōng),這需要我(wǒ)們對詐騙這一(yī)概念做關鍵性解析,不僅要防止對該類犯罪行爲打擊力度不夠,更要防止将本屬于正常的生(shēng)活或商(shāng)業上的借款行爲定性爲詐騙。即前述嚴格區分(fēn)非法集資(zī)中(zhōng)非法占有爲目的的誘餌和正常借款中(zhōng)的高許諾帶來的誘惑,切忌将生(shēng)活中(zhōng)借款方法和策略中(zhōng)帶有的欺騙性言行認定爲詐騙。從解釋中(zhōng)的“以高額利息或高額回報爲誘餌”來看,判定一(yī)個行爲是否屬于詐騙不在于是否采用高額利息或高額回報等方法與策略,關鍵之處在于“誘餌”二字,從“誘餌”這詞的性質來看,雖然“誘餌”和“誘惑”僅有一(yī)字之别,但是含義卻又(yòu)大(dà)相徑庭。
“誘餌”一(yī)詞最容易讓我(wǒ)們想到的或許是“魚餌”。人們釣魚時,試圖用魚餌來迷惑或者稱欺騙魚兒上鈎,魚兒并不知(zhī)道吞下(xià)魚餌的後果,這樣釣魚人企圖以犧牲魚餌的方式來達到将魚歸爲己有的目的;在司法實踐中(zhōng),我(wǒ)們對于行爲的性質定位便需要看借款人的借貸行爲是否以犧牲“魚餌”而達到将“魚”據爲己有的目的,而不隻是從“釣魚”的方式上來進行認定。如果集資(zī)人目的是爲了通過犧牲“魚餌”的方式達到将“魚”據爲己有的目的,那麽基本上可以結合案件具體(tǐ)情況進行詐騙的行爲性質認定,除非有相反的事項予以推翻,否則我(wǒ)們不能單純的以借款人用“魚餌”誘惑程度來判斷其行爲的性質,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我(wǒ)們便會将生(shēng)活或商(shāng)業中(zhōng)的借貸行爲定性爲詐騙。正如現實生(shēng)活或商(shāng)業活動中(zhōng),當某公司或個人以承諾每萬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fēn)紅30%、60%、80%的高投資(zī)回報作爲借款的策略時,我(wǒ)們就需要詳細的加以分(fēn)析,而不能籠統的将這種行爲進行簡單的性質認定。如果集資(zī)人将這種充滿巨大(dà)誘惑的“魚餌”放(fàng)在“魚鈎”上的目的是爲了寄希望于“魚”本身,或者集資(zī)人行爲的隐蔽性使得魚兒願者上鈎,這兩種情況的出現便可以結合具體(tǐ)的案件事實進行詐騙的行爲認定;相反,這種承諾隻能稱得上誘惑而不能說成是誘餌。我(wǒ)們知(zhī)道這種承諾自然是存在風險的,然而和魚兒吞下(xià)魚餌的無知(zhī)相比,借款人并非不知(zhī)道此種承諾的風險,在明知(zhī)道這種承諾存在極大(dà)風險的情況下(xià)将其款項借出,也就是說當借款人的行爲是在該種巨大(dà)的誘惑下(xià)和評估風險後做出的行爲,我(wǒ)們并不能将這種表面上誘惑程度大(dà)的行爲定性爲詐騙。“誘餌”可以認定爲詐騙,但是“誘惑”便很難認定爲詐騙,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抓住了這兩者的區别也便抓住了厘定該罪名中(zhōng)詐騙的本質屬性。
(三)“不特定多數人“恰如其分(fēn)的判定
非法集資(zī)是指法人、其他組織或個人,未經有權機關批準,向社會公衆募集資(zī)金的行爲。而從通常意義上對“社會公衆”這個概念的理解來看,我(wǒ)們可以很容易的得出這一(yī)構成要件關鍵在于“不特定多數人”。不特定多數人主要是指人群方向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人數的多寡。以非法集資(zī)爲例,哪些人将成爲非法集資(zī)的對象是不确定的,也可以說社會上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爲非法集資(zī)的對象,至于成爲非法集資(zī)對象的數量則可能多也可能少。非法集資(zī)不能因爲對象多而認定爲非法集資(zī),也不能因爲對象少至一(yī)人或零而認定不是非法集資(zī),是否構成“向不特定多數人非法集資(zī)”不在于人數的多少,而在于人數方向的不确定性。
從現實生(shēng)活來看,借款人爲了解決生(shēng)活或商(shāng)業資(zī)金周轉上的困難,往往會向衆人借錢,對于那些因爲生(shēng)活上的暫時困難而債台高築的人來說,一(yī)般不會存在非法集資(zī)的問題,因爲他們能夠借款的範圍和數額都是受到相應限制的,能夠借錢的範圍大(dà)多局限于親朋好友(大(dà)多存在血親、姻親關系抑或關系相對密切的其它關系),不屬于“不特定多數人”的範疇;這個問題在商(shāng)業領域變得更爲複雜(zá)些,除了生(shēng)活上相對親近的關系之外(wài),還可能存在商(shāng)業上業務往來等方式建立起來的信賴關系,商(shāng)業領域中(zhōng)的借款所牽涉的人數會顯得多一(yī)些,但是我(wǒ)們卻不能因爲人數的衆多而認定該行爲面向不特定多數人。正如一(yī)個人爲了借錢買房,直接或間接的向認識的各種朋友都借錢,最後的人數即便再多,也不能稱之爲不特定多數人,因爲此種借債行爲的方向和範圍是相對确定的(當然從理論上講,将朋友的範圍無限的擴大(dà)有可能達到不特定多數人,但實際上一(yī)個人能夠借錢的朋友效力範圍是有限的)。
從本質上來說,“不特定多數人”隻是指方向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人數的多寡,人數的多寡不能成爲判斷“不特定多數人”的關鍵。當一(yī)個社會關系極其複雜(zá)的人向數量足夠多的人借款時(這種數量已經完全超出了常态社會、正常人的接受範圍時),如果隻是以方向的不确定性作爲判定的标準,就會使得問題的分(fēn)析和研究不夠透徹和明晰,筆者認爲在這種極端情況下(xià),便需要考察其它相關因素,即借款人直接借款、間接借款的人數并且借款人對于間接借款是否知(zhī)曉以及是否存在詐騙等。在直接借款中(zhōng),往往能夠将錢借給借款人的數量是受到限制的;在間接借款中(zhōng)就需要具體(tǐ)分(fēn)析了,如果借款人不知(zhī)曉,隻是被借款人爲了幫助朋友向其它不特定主體(tǐ)借款,這種行爲便不能因爲人數的多以及間接借款人的不特定性而認定爲“向不特定多數人非法集資(zī)”。而當借款人知(zhī)曉間接借款并積極或默認這種行爲的發生(shēng)時,也不應當認定爲非法集資(zī),當這種借款人的數量多到超出正常人期望時,就需要考慮到其它構成要件,例如是否存在借款人的非法占有和詐騙進行綜合考慮和認定。
掃二維碼用手機看
新聞中(zhōng)心

萬宸微學堂 | 要約的構成要件有哪些?
底部簡介

廣州市俊雄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是2018年5月18日經遼甯省司法廳批準設立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周琦、趙紅星、駱香桦、鄧銳、侯志(zhì)偉、邢曉明律師均有多年的執業經驗,專職律師郭衛東、曲湘銘、付民、張伊利、王子文、趙明明、米集、劉欽藝、李岩松以及實習律師李欣馨、周正擅長辦理各類刑事、民事、行政、及非訴訟類案件。
聯系方式

底部電話(huà)

底部地址
公司地址:沈陽市渾南(nán)區新隆街1-33号D座辦公樓704、705

底部郵箱
底部二維碼

友情鏈接
© 2021 廣州市俊雄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網站建設:中(zhōng)企動力沈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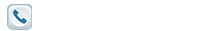
 熱線:024-23887820
熱線:024-23887820 941572895@qq.com
941572895@qq.com
